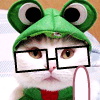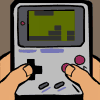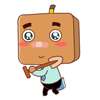唐代诗人郭震的《宝剑篇》开篇以厚重的笔调渲染出铸剑时的雄壮景象:
“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皆赫然!”
两千余年前,这一景象就出现在南京朝天宫所在的冶山之上,而这里的历史甚至比这座城市的历史还要久远。

史载,吴王夫差曾在此设立冶城,著名的铸剑大师干将、莫邪就在此打造兵刃。或许,今天依然在博物馆闪耀着寒光的吴王夫差戈就是在此铸造的。还有那传说中斩落君王首级的神兵干将、莫邪也有可能在此诞生。再过了数十年,南京最早的城市越城方才出现。不过,冶城仅仅是一座大型作坊,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朝天宫所在地被称为冶山,就是从此得名的。

可以想见,二千多年前的冶山之上,青烟紫气直冲天际,红光烈焰点亮夜空,雷鸣般的敲击声昼夜不息,与城下江流的咆哮声时时呼应。在这巨吼中,吴王夫差将江南抛在身后,直奔中原而去,他踏上了天下争霸的道路,走向自己人生的顶点,这也是毁灭的开始。经历了数十年的龙争虎斗之后,昔日的霸主与野心都已随风而逝,唯有这座昔日的作坊依然矗立,还在继续将一把把寒光四射的兵器锻炼成型,让列国胆寒。至今流传下来的的越王勾践剑,是否也同样从此而出?就在它的南方不远处,一座辉煌的城市已经开始奠基了,并且一座城市的灵魂也开始铸就。

时间流逝过数百年,另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第一次将南京设为了首都,在这里,冶城继续作为兵器冶炼作坊存在,上个世纪考古学家曾在此发掘出吴代冶炼作坊的遗址。昔日的雄心壮志再次被点燃,随着滔滔江水汇向辽阔的海洋之中。吴国曾数次谴船队出海,北至辽东,南至南洋诸国,冶城此时正处于江边,也曾一次次目送给浩大的船队扬帆远航。不知这些远行者是否在此刻回望过故乡,那江南的烟雨是否伴着海潮夜夜入梦。孙权的几次远行似乎均无功而返,那令强虏灰飞烟灭的豪情也随着其创立者的衰老而渐渐逝去,但却也留下了一个有关热血男儿的故事。
史载,当时吴国遣使通好割据辽东的公孙渊,而首鼠两端的公孙渊杀死吴使,其余秦旦、张群、杜德、黄强等六十余人被公孙渊分置于玄菟郡(在今天朝鲜平壤一带)中。他们试图杀死郡守,劫夺此郡,但被人告发,只能越城墙逃走。在路上,张群腿伤发作,跟不上同伴,杜德则搀扶着他一起走。这些与家乡远隔万里的人们就这样相互扶持着在异域的崎岖山谷中行进,走过了六七百里的山路。张群无法再向前去,要求同伴留下自己,自谋生路。杜德说:“万里流离,死生共之,不忍相委。”那几个沦落异乡的身影,在荒凉的山谷中抱头痛哭,天地茫茫,但他们找不到回家的方向。在帝王心中,他们也许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工具,但他们却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同样有着自己的家庭,有着自己的生活。最终,杜德留了下来,采集野菜野果谋生,而让同伴先走。所幸秦旦、黄强到达了高句丽,说动了高句丽的位宫王。位宫派遣人接到两人,并将他们送回了吴国。史载“旦等见吴主,悲喜不能自胜。吴主壮之,皆拜校尉”。

吴国之所以设冶城于此,是因为南京这一带出产铜、锡、铁,这些均是冶炼兵器的原料。尽管后来此地已无了兵器铸造之声,但铜铁尚存,金石之气亦不时一现。
《世说新语》曾载王羲之与谢安同登此山的故事: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世说新语 言语第二十一》)
王羲之虽为一代名士,但心中雄豪之气不减,自然对当时以清谈避世的谢安有所不满。登临冶城,凭吊昔日强兵冶铸之所,虽语气平淡,但其中棱角毕现,一如脚下这暗蓄破空之想的冶城山。相较而言,谢安之话虽然简短,但内蓄更深。晋初的王敦、苏峻、祖茂皆以大将身份叛乱,建康城也因此历经浩劫。此刻桓温兵势正盛,不臣之心已蓄,后来的桓氏之乱已经初显征兆,此刻的谢安以清谈避世,以商鞅警右军,对后事已有预感。日后桓温暴死,东晋暂时度过危机,谢安东山再起,开始独挡一面。当前秦百万大军压境之时,谢安同样狮子奋迅,尽谴家中子弟,一战而破敌。可见,谢安也并非空谈之士,心中亦不乏百万大军。南京城能历经劫难终又烈火重生,其中的豪气亦不减当年。

时隔一千余年,当太平天国大军攻克南京,官僚豪绅都做鸟雀散之时,却有一文弱书生筹划大谋于城中。张继庚,江宁人,国子监诸生,幕游湖南,助守长沙,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南京被围,募兵守城,献谋御敌;城陷后,结同志,招友军,已离险地,仍返孤城。其后被擒,仍施反间计,称太平军中忠勇之士为其同谋,杀百余人,慨然赴死,坦然受刑。
过去提到他,多因其破坏农民起义将之塑造成阴险的间谍形象,可身陷孤城之中依然斗志不减,数离险地却以破敌为己任,再入虎穴,亦可称为壮士。清末南京著名诗人、学者孙文川为之写《张烈士行》,百余年后读来依然铮铮然如金石鸣。诗曰:
“不破一甲折一矢,数十贼魁同日死。
贼自杀贼谁所使,死不忘君一烈士
……
金陵节烈俱捐生,烈士铁中之铮铮。
一息仅存尚报国,临危不乱尤难能”。

而其人故宅就在朝天宫附近,屋边有白果树,民国初年尚存,前清举人王孝煃有《冶西杂咏》三十首,其中多载朝天宫附近典故,有一首诗就描写张继庚故宅白果树:
“是非成败且休论,气节功名第一层。
多少故家零落尽,尚余乔木荫西城”。
诗句虽有些直白,但沧桑之感,悲壮之气亦令人动容,可与刘禹锡的《朱雀桥》相呼相应。朝天宫虽已为衣冠会聚之所,可昔日的雄壮豪情,亦在这些文弱书生身上闪现。

孔子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而君子居之。”隐忍无道,蕴大志于胸,这是看似柔弱的南方人坚强的一面。朝天宫自明太祖将之设为江南府学以来,除在太平天国时期被改为屠宰场外,一直都是莘莘学子诵读经典的场所。可以想象,当年的朝天宫一定是书声朗朗,走入此地,必然肃然起敬。然而,回想二千余年的世事浮沉,人世变幻,这里何尝没有那敢于挺身而出的忠烈之士?或许,在干将、莫邪在此铸剑之时,就已经铸就了这里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