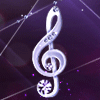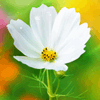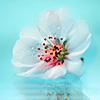【摘要】“包衣”是清代旗人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清代皇族的私属,由于他们双重的身份及其与皇室、内务府的特殊关系,使包衣群体的研究成为清代政治与旗人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学界在“包衣”称谓的解释和身份的认识上并不清晰。本文在梳理学界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包衣、阿哈、包衣阿哈以及家人等不同称谓的辨析,明确“包衣”是清代包衣组织成员的专称,不能用阿哈、包衣阿哈或家人替换。
【关键词】 清代包衣奴仆身份
【说明】本文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内务府与清代政治社会》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号( 10JJD770020) 。
【文章来源】《清史研究》2013年第1期。
作者祁美琴 崔灿
清初满族社会与清代旗人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主奴关系,清代用以称呼“奴仆”的名称也有多种,如阿哈( aha) 、包衣阿哈( booi aha ) 、包衣( booi ) 、家人( booi niyalma) 、辛者库( sinjeku) 等等。不同的称谓不仅体现了当时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也代表着各自不同的身份差别。虽然已有学者对此进行过辨析,笔者早年也曾作过探索①,但是一些正确的结论,并未在学界形成共识,如在具有代表性的《满族大辞典》和《清代典章制度辞典》中,表述就存在差异,前者释包衣指内务府,或“内务”; 后者则谓包衣即家奴,与阿哈含义相同,是包衣阿哈的简称。②二者的解释大相径庭,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就这些概念的含义和彼此的异同,再做辨析。
一、学界观点介绍
关于包衣,最早的研究见于孟森先生的《八旗制度考实》(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 年) ,文中说: 考包衣之名,“包”者,满洲语“家”也; “衣”者,虚字,犹汉文“之”字。八旗“别设包衣参领佐领,则专为家之舆台奴仆,即有时亦随主驰驱,乃家丁分外之奋勇,家主例外之报效,立功后或由家主之赏拨,可以抬入本旗……其初八旗本无别,皆以固山奉职于国,包衣( 二字原不成名词,后则作为职名) 奉职于家。其后上三旗体制高贵,奉天子之家事,即谓之内廷差使,是为内务府衙门。”这里,孟森先生主要是从八旗制度下包衣组织分工的角度,讨论包衣与一般旗人的职责和身份差别,而并非是对“包衣”群体的定性分析,也未涉及其他奴仆概念。其后,郑天挺在《清代包衣制度与宦官》( 《清史探微》1943 年) 一文中,对包衣的性质有了较为详尽的解释,摘要如下:
“包衣”即是“奴仆”,在法律上,他们的隶属、居住、生活、婚娶全无自由,而且他们的奴籍是子孙相续的,非得主人允许不得脱离。所以就性质而言,包衣就是私家的世仆。不过有一点应该注意,就是包衣之所谓奴仆,只是对他们主人而言,他们可能另有自己的官阶,自己的财产,自己的奴仆。包衣制度发生在八旗制度③ 之前,所以清初的宗室贵戚勋旧,无论是否主管旗务全有包衣。太祖起兵时追随的人很多,这些人全是后来的勋戚,他们全有给使的仆役,就是包衣。当时旗制未定所以未尝加以限制,旗制既定亦未尝因之取消。但包衣的主人、爵秩有尊卑,地位有高下,因而包衣也有等差。包衣之下还用包衣,主人之上仍有主人。所以有一时期,分隶上三旗包衣佐领下的皇帝包衣,与分隶下五旗包衣佐领下的王公包衣,以及勋戚功臣家的包衣,其他私家的包衣,统称包衣,一无差别。逮后包衣制度日严,名称相同易于混淆,私家“包衣”渐改他称。家仆、旗下家奴、八旗户下家奴实在就是私家的包衣,因为要别于旗制里的包衣,所以改称。
郑先生的观点概括起来有三点: 一是包衣的性质是奴仆,且是私家世仆; 二是包衣制度出现在八旗制度之前,且清初( 暂且理解为入关前) 无论皇帝、旗主还是勋戚功臣之家的私仆均称包衣; 三是所谓的“逮后”( 暂且理解为入关后) 包衣成为旗制里的包衣的专称,家仆、旗下家奴、八旗户下家奴的名称开家仆、旗下家奴、八旗户下家奴的名称开始出现。
其后,莫东寅在他的《满族史论丛》( 1958 年版) 中,对早期满族社会组织和社会阶层做了最完整的论述,在对“奴隶”阶层的阐述中,将清初所谓的“奴”或“奴隶”阶层成员,均冠之以“包衣”称谓; 指出包衣即家里的人,也就是奴隶。与郑天挺的观点一样,他也认为包衣之制远在旗制出现之前就有了,清初宗室贵戚勋旧全有包衣; 入关以后,包衣制演化而为内务府制度。至于私家包衣,渐改他称,即所谓“家仆”、“家奴”。
以上三位学者,基本上奠定了学界有关“包衣”的解释及其性质判断上的观点。其共同之处是,基本上未涉及阿哈、包衣阿哈、家人的解释; 虽然莫东寅的观点隐含了包衣就是阿哈的论点。此后,随着有关研究的深入,学界在使用这些称谓的时候,开始进行更明确、更具体的说明和解释,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论点:
( 一) 包衣是“奴仆”的统称
周远廉在《关于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问题》( 《社会科学辑刊》1979 年4期) 一文中提出: 早期满族社会的“奴隶”是“阿哈”,全名为包衣阿哈,是满文的音译。但是,第一次对清初及清代奴仆称谓及其关系作系统阐述的是杨学琛先生。她在《从〈红楼梦〉看清代的八旗王公贵族》( 《红楼梦学刊》1982 年第4 辑) 一文中讲: 包衣,全名包衣阿哈,意为家之奴仆,有时写作阿哈,家下人,户下人,旗下家人,壮丁或庄丁。包衣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编隶八旗包衣佐领的包衣,称为“包衣旗人”。另一类是附于家主户下的包衣,一般称为“户下人”或“旗下家人”,包括“壮丁”、“庄丁”、“牲丁”和“家人”等等,其身份地位远远低于“包衣旗人”。这里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是继郑天挺之后,第一次注意到清代奴仆的不同称谓,并试图辨析其差异。但是她辨析的前提是将“包衣”作为“奴仆”的统称本身,却是模糊了“包衣”的特定身份,成为学界混淆“包衣”与“阿哈”概念的滥觞。从此,类似的观点就充斥在清史学界,典型的表述为: 包衣,满语“包衣阿哈”的简称,亦简称“阿哈”,意义为家奴。
( 二) 包衣是部分“奴仆”的称谓
笔者所见,最早尝试区分包衣和不同“奴仆”称谓之间关系的是左云鹏的《清代旗下奴仆的地位及其变化》一文,他指出“奴仆因其所服劳役之不同,又有‘包衣’和‘壮丁’的区别。包衣是家内服役的奴仆; 壮丁则是为主人耕种田地的奴仆。这两种奴仆,因其和主人的接触不同,关系不同,因而其后日地位的变化也就有所不同。”④乌廷玉则进一步说,包衣阿哈通称壮丁⑤。而马协弟则对“包衣阿哈”与“阿哈”作了区分,认为“奴隶,满语叫阿哈,包衣( 家内的) 阿哈,一般指的是在奴隶主家庭内服役的奴隶。”⑥王钟翰先生在《清朝满族社会的变迁及其史料》一文中,讲如何运用史料观察满族社会的变迁时说到: 满文档册中的包衣 booi) 、包衣阿哈( booi aha) 和阿哈( aha) 在交换使用着,其内涵不无细微差异。⑦ 只是没有再进一步的阐述。总体上看,上世纪90 年代前后,一些学者再次注意到了“包衣”作为“奴仆”统
称的观点的局限性,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开始讨论不同“奴仆”称谓之间的差异及其群体身份问题。
(三) 包衣是专称
陈国栋谓: 八旗都有包衣。在最初时,包衣本即八旗旗主私家的亲军兵弁或奴仆。⑧ 这大概是学界首次明确提出包衣的领属者是“八旗旗主”的观点。傅克东在《从内佐领和管领谈到清代辛者库人》一文中则称: 包衣即皇家奴仆的身份地位,比起清帝所说的“八旗世仆”来低人一头; 但比起旗人的户下奴仆来,却又高出一等。⑨ 这是从人身隶属关系上,进一步明确“包衣”是皇家世仆的专称。杜家骥则是从组织关系上,指出“包衣”是包衣佐领、管领下人的专称,与一般的旗下家奴有别。旗下家奴,或称旗下家仆、八旗户下人、旗下家人等,这些人没有独立的户籍,而附于旗人主人家的户下。包衣的地位高于旗下家奴。⑩以上因作者关注的角度不同,说法有别,但仔细辨析,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因为八旗包衣佐领、管领的领有者是皇帝和宗室王公,他们都具有旗主的身份,故而结论相同: 即包衣是包衣组织成员的专称。
以上三种不同的解释和认识,笔者认为最准确的应该是第三种,但是目前学界盛行的说法却是第一种。因此这里有必要就“包衣”的称谓和身份做进一步的讨论。
本文主要辨析三个问题: 一是阿哈与包衣阿哈的关系; 二是包衣与旗下家奴即“家人”的区别; 三是包衣的身份和地位。依据的文献主要有三种: 1、清初满文档案。现存反映清初满族社会历史的满文档案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满文老档”。(11)“满文老档”所记史事从丁未年(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到天聪六年( 1632) 较为完整; 崇德以后事只有崇德元年纪事。一是“内国史院档”(12)。“内国史院档”所记包括天聪元年至崇德八年( 缺崇德六年) 及顺治朝史事,恰好弥补了“满文老档”记载上的缺憾。这两部分档案,前者详努尔哈赤时期事,后者详皇太极时期事,二者连接互补,从而形成清军入关前这一重要时段的较为完整的原始资料,为我们研究清初满族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较为充分的文献依据。2、《清实录》。清历朝汉文实录是探寻清统治者观念和行为的较好文本,尤其是对我们辨别一些概念在当时的意义有重要的参照作用。3、其他如《八旗通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等。“通谱”列有大量的“包衣”的家世及其事迹,可以提供许多翔实的个案及统计资料,帮助我们认识这一群体。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是在梳理这些史料中所出现的“阿哈”、“包衣阿哈”、“包衣”、“家人”等称谓的使用情况后而得出的。
二、包衣阿哈与阿哈
“满文老档”中第一次出现“包衣阿哈”一词是天命三年四月,记述抚顺投降人户所属时,令“因战事而失散之兄弟、父子、夫妇、亲戚、家奴( booi aha) 及一应器物,尽查还之。”(13)天命五年九月,在大贝勒代善与努尔哈赤的一段对话中,有“不赐我以僚友、国人,不给与家奴( booi aha) 、牛羊马群,或不丰足供给衣食”一句(14)。从上下行文看,可以确定这里的包衣阿哈是作为奴仆的群体身份的称谓而使用的。与此同时,在包衣阿哈称谓出现的场合,阿哈常与包衣阿哈并用。如:
天命六年闰二月十六日,努尔哈赤谕曰: “贝勒爱诸申,诸申爱贝勒; 奴才爱主子,主子爱奴才。奴才耕种之谷,与主子共食; 主子阵获之财物,与奴才共用,猎获之肉,与奴才共食……著勤于植棉织布,以供家奴穿用,见有衣着陋劣者收之,交与善养之人等语。”(15)四月,努尔哈赤在提到逃人事件时,称“昔吾国家奴之遁逃,皆以无盐之故也! 今且有之”。(16)
此处译汉“奴才”、“家奴”,即满文的阿哈和包衣阿哈。在不同语境、同样语意的表述中,努尔哈赤分别使用了“阿哈”与“包衣阿哈”,说明二者含义相同,指代同一群体。事实上,对于当时满族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奴仆”身份的人群,在满文中均是以阿哈或包衣阿哈来指称。举例如下:
天命六年六月二十日,“审理之事: 攻辽东时,张邱携来其幼子,托一甲士看护。又其家奴( booi aha) 以盗取之缎衣送与众人,并报执法者,遂免刺其奴仆( aha) 之耳鼻”(17)。七年六月十九日,努尔哈赤谕令大臣等应赡养新附蒙古,供给食物,令“赐给蒙古之奴仆与包衣阿哈一同兼管,伐薪煮饭等皆令一同操做。或逃或失,由尔偿之”(18)。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执魏生员所控之七乡六十四名男丁,经佟参将、拜音达里讯问,有十八名男丁供称: 我等七乡之人谋叛是实”。遂许招认者父母妻子安然度日,家奴( aha) 耕作田地。二十七日,因叶赫之锡林擅杀逃往之汉人,被其家奴( booi aha) 首告,革其备御职,首告之奴( aha) 准其离主。(19)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清军征服朝鲜,朝鲜国王“负罪”拜谒时,皇太极给还多尔衮之前克江华岛时所虏获的王室及臣僚等,给还的人口中,除妻子儿女之外,还有奴仆( aha) 。此处对于同一满文表述的“阿哈”,汉译者分别用了“奴”、“奴仆”、“家奴”三种指称。(20)
上述档案史料中,凡是满文“aha”,在意译为汉文时,多以“奴仆”或“仆”对译;但是也有译为“家奴”的时候。而凡是满文“booi aha”,在意译为汉文时,多译为“家奴”、“家仆”,但是也有译为“奴仆”的时候。说明在汉译者看来,二者关系密切,在互相替换的语境中,不影响满语原意。正如《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的译者谓: 阿哈,义为奴隶、奴仆。入关后为奴才。汉意为家奴。《实录》为奴仆。包衣阿哈,义为家奴。《实录》为家仆、奴仆。明确指出二者均有“奴仆”、“家奴”的涵义。从词义本身看,“包衣阿哈”实际上是一个短语“家里的阿哈”之谓,包衣是“阿哈”的定语成分,“包衣阿哈”应该包涵在“阿哈”中。因此,可以确定“包衣阿哈”与“阿哈”身份相同。
不过,从阿哈一词出现的语境所看,阿哈的指代更多官奴性质,多用于被赏赐的对象或笼统言之,而包衣阿哈主要是针对其原有主人而出现的称谓。为了更进一步明晰二者的身份涵义,这里我们将对史料中的“阿哈”群体的身份进行全面的考察。在以下征引的档案文献中,凡是出现“奴仆”或“仆”的汉文词汇,均为满文“阿哈”的意译。据笔者对入关前满文档案的粗略统计,使用阿哈称谓的场合,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 一) 被赏赐的对象
档案中大量有关“奴仆”的记载是与赏赐联系在一起的。如万历三十六年( 1608 )三月,在记述舒尔哈齐过错时称: “聪睿恭敬汗之弟舒尔哈齐贝勒系唯一同父同母弟,故凡国人、贤良僚友、敕书、奴仆,以及诸物,皆同享之。”努尔哈赤强调指出,这些国人、奴仆非为父所遗留,而是“兄我所赐”。(21)
后金国建立后,赏赐奴仆的记载大量出现: 天命三年二月,赏来归的东海使犬部人妻子、奴仆、马、牛、衣物、粮食、房舍等物。四月,赏赐抚顺降将马、牛、奴仆、衣物、粮食等。十月,呼尔哈部首领纳喀达率百户来归,努尔哈赤具盛宴接待,并赐为首八大臣各奴仆10 对,次者5 对,再次者3 对,以供役使,并赐马、牛、衣物等。七年三月,蒙古科尔沁的囊苏喇嘛在努尔哈赤处圆寂,努尔哈赤专门赐一“汉人屯堡”,令囊苏喇嘛属民63户安葬、守护墓地,并赐其弓、甲、马、骡及差使的奴仆男妇50 对。(22)天聪八年二月,加赏祖可法人10 对,牛11 头。令其编为庄屯。(23) 崇德元年十月,赏赐归降明将巢丕昌奴仆30对,梁和、刘银柱奴仆2 对等。赐锦州降将胡有升奴仆40 对,赐张绍祯、门世文奴仆各30对,赐秦永福、门世科奴仆各20 对,以及马、牛、骡、驴、财物等。(24)
类似的场合中的“阿哈”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多以男妇各一搭配成“对”赏赐,显示出将“人”以“物”比附的属性。二是这些被赏赐者主要来自俘获人口。如天聪二年二月初,清军征察哈尔多罗特部,俘获11200人,只将其中的蒙汉男丁1400 名编为民户,“余俱为奴”。天聪四年三月底,清军招降榛子镇, “以民半数编户,半数为俘”。六月,皇太极在议阿敏之罪时,其中之一就是“尽略( 榛子镇) 降民牲畜衣物,驱该城汉人至永平,分给八家为奴”。崇德元年八月,皇太极令驻守海州河口伊勒慎等将俘获的明朝捕鱼男丁22 人,交与尚阳堡富民为奴。(25)
由于将大量的俘获人口分拨给八旗将领、官员人等,致其拥有大量的私属人口以供役使,数额从几十至上千不等。天聪八年正月,因众汉官以差多赋重向户部贝勒德格类诉苦,德格类驳斥时谓:
我国小民穷,若从明国之例,按官职给俸,势有不能。蒙天眷佑,获有财物,向按功爵,加以赏赉,所获土地,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先汗方拨辽东人时,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以下照功次拨给。若尔等所谓照功次而行之言,果出于诚心,则满汉官员之家奴,理应相均,乃尔汉官或有千丁者,或有八百丁者。余皆不下百丁……(26)
这些大量的分赏给各级将领官兵役使的私属丁口,就是阿哈。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哈与那些同时被分配的牲畜、财物一样,是主人“会说话”、能够创造新财富的财产和工具。这些人是后来旗下庄丁、家奴的主要来源。
( 二) 罚入辛者库
在史料中,经常出现官员、旗人获罪,籍没为奴( aha) 。这些所谓“籍没为奴”者,即是罚入“辛者库”为奴。清代无论上三旗还是下五旗的包衣组织中,均有辛者库; 但辛者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组织机构,而是一种罪籍身份。与前文中被赏赐的“阿哈”领有者不同,由于他们隶属于包衣组织,故有资格役使这些辛者库人的,自然就是那些具有旗主身份的努尔哈赤家族成员。
天聪七年九月,“满文档案”在述雍舜晋级缘由时谓: 雍舜原为二等参将,后削职没入贝勒家为奴。至是以善战被创,“升奴”为二等参将。八年十二月,三等梅勒章京丁启明卖汗所赐衣物,被家奴首告,革职,给本贝勒家为奴。九年八月,议管理汉人官员功过,佟三因所管人丁增不抵损,革去旗鼓,给本贝勒家为奴。(27)崇德元年六月,率兵出征呼尔哈部的吴希特依等五将领以失职罪贬为奴,其本身夫妇及所属奴仆,给和硕豫亲王、和硕肃亲王、阿拜阿哥、安平贝勒等为奴。(28)
这里所述的将获罪者赐给贝勒家为奴,实际上即是入“辛者库”为奴。如上述雍舜曾没入贝勒家为奴一事,在《八旗通志·初集》中有更详细的记载: 雍舜,因天聪三年、四年随太宗征明期间建功,授二等参将世职。缘事革,没入辛者库,给贝勒家。七年,随贝勒德格类征明攻旅顺口,首先登城,中炮伤一,枪伤一,箭伤五。寻叙功,以善战被伤,脱辛者库籍,复原职。(29)
类似的记载有很多。如天命六年闰二月,牛录下诸申弃甲败逃被没入旗主贝勒家为奴。六年十二月,崩阔里诬告塔拜阿哥与其儿媳私通,审拟鞭一百,给大贝勒为奴。(30)天聪四年六月,论弃滦州、永平诸臣罪,松果图备御革职,籍没家产,以其夫妇给墨尔根戴青家为奴; 恩特依游击革职,籍没家产,其夫妇给汗家为奴; 爱木布禄,籍没家产,以夫妇给大贝勒家为奴。六年二月,议临阵退缩诸臣罪,“锦州之役,永顺退缩,并遗弃本牛录负伤人”,抄其家并赐与贝勒为奴。八月,以游击雅本布鲁、备御董山出征察哈尔时遗弃粮米,不驻约定之地,获罪,“革职抄家,夫妻净身出户,给各贝勒家为奴”(31)。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罚入辛者库“奴”籍者,主要是八旗官员和披甲。在战争年代,他们可以通过立功而脱其“籍”,重新回到旗人的主流社会中。典型的事例如宁完我:
崇德元年二月,宁完我( 汉军正红旗) ,原系萨哈廉贝勒家奴仆,因通文史,汗擢至文馆,参预机务,授为二等甲喇章京,准袭六次,赐庄田奴仆。征北京时,令宁完我留守永平府,以赌博为李伯龙、佟正首告,审实。汗宥其罪。汗知其行止不端,屡加诫谕,竟不能改。后复与
大凌河归附甲喇章京刘思宁赌博,为刘思宁家人告发,审实,拟宁完我罪,革其职,凡汗所赐诸物,悉数夺回,解任,仍给萨哈廉贝勒为奴。籍刘思宁诸物,发南阳堡为民。(32)
因辛者库籍隶包衣组织下,故有的史料记载获罪受惩罚的官员时,直接记为籍没后编入包衣牛录。如顺治十一年十月,议政王大臣会议从敬谨亲王征湖南败绩诸臣罪:
学士马尔都,隐匿失陷情由不奏,革职,籍其家,鞭一百,入包衣牛录。侍读学士硕对,隐匿不奏,革职,籍其家,鞭一百,发入本王包衣下。(33)
顺治十五年八月,宗人府等衙门会议福建罗源县对敌败遁之将领罪,其中甲喇章京一等阿达哈哈番何尔敦、郎中扎穆尔、员外郎胡世礼、拜他喇布勒哈番萨弼图、硕色等,“伊父叔及兄曾阵亡,应免处绞。革职,籍没,鞭一百。入包衣牛录为奴。有父职者准以兄弟承袭”(34)。顺治十七年三月,兵部以海寇失陷镇江,巡抚蒋国柱、提督管效忠等败绩遁走,分别定议奏上。得旨:
蒋国柱免死。革职,与本王下为奴。管效忠免死,革提督并世职。鞭一百,发包衣下辛者库为奴。俱籍没家产……牛录章京喀福纳、查都、拖辉、布颜、希佛讷,俱革职,免死, 鞭一百, 籍没为奴。(35)
康熙二十二年,在平定三藩之乱中,都统觉罗巴尔布因贻误军机,拟立绞,籍没家产,妻及未分家子编入包衣佐领。副都统托岱、宜思孝,因丢失城池,拟立绞,籍没家产,妻及未分家子编入包衣佐领。又精奇尼哈番硕塔因弃城奔回,法应处死,但因有免死谕,拟革职、鞭一百,籍没家产,本身并妻及未分家子编入包衣佐领。又尚书哈尔哈齐因攻伐不力,拟立绞,籍没家产,妻及未分家子编入包衣佐领。都统觉罗画特因在交战中不收官兵骸骨并失炮位,拟革职,籍没家产,编入包衣佐领。在这些拟罪的高级将领中,除画特系出身觉罗,编入包衣佐领为奴“似属不便”、免其编入外,其他人均入包衣下辛者库籍。(36)
辛者库人虽以“奴”称,但是因为其特殊的来源和隶属关系,他们与包衣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有无职位和俸饷上。在其他方面则与普通包衣人的身份相同。如有关旗人免发遣的法令中,对辛者库和包衣人并无区别。雍正四年曾定例,汉军暨辛者库、包衣佐领、旗鼓佐领人等犯军流者,俱按所犯编发各省地方; 乾隆二年改汉军发遣例,仍以枷责完结时,以辛者库、包衣佐领、旗鼓佐领人等与汉军同属旗人,亦准照免发遣旧例办理。(37)
这些事实说明,辛者库人虽是奴仆,但却是包衣组织下人,有旗人户籍和相应的“金斗粮”待遇,故不能与普通的“户下奴”相比。同时,辛者库在上三旗包衣组织中,是附籍于管领下。
康熙后期,随着入辛者库籍人员的增多,这些人反而成为包衣组织管理中的负担。为此,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康熙帝谕令内务府: 各处治罪籍没家产解来优劣者甚多,既无用,何必徒食粮饷,除原在者不动外,将此等解来者或赐给阿哥、公主等,或赐给村庄之处,妥加议定办理。随即内务府议准: “现由三十内管领各处治罪及籍没家产解来之人内,一并交由阿哥分配及送与公主,将无业、无用者分别赐给村庄。嗣后各处治罪押来、籍没家产入辛者库者,内满、蒙、高丽、废员、工匠等众留于管领内。不可留管领之汉人家奴赐给村庄可也。等因具奏。奉旨: 依议。”(38)所以,康熙五十七年四月,当受太子案牵连而被治罪的正黄旗、正红旗的朱都讷、朱天宝、常赖、戴保、金宝等人之“妇孺”,拟罚入内务府为奴时,康熙帝不准其进入紫禁城等要地,且令“将此群人”平均分赏给弘曙、弘。此后,对于“籍没为奴”罚罪的适用范围的限制及包衣三旗辛者库人的分拨的事例,也说明入“辛者库”为奴,对于其“主”而言,主要是起管理作用,而非役使。如: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允禄为宽免无力还欠者入辛者库而奏称:
查得,从前八旗亏欠钱粮之人,该旗并不虑及罪由、亏欠银多少,凡期满不能完者,立即参奏。倘原主,或系子孙治罪后,子、妻充上三旗及下五旗公中佐领者,入内务府辛者库。倘属下五旗者,入各王公家辛者库。又有旗行文内开: 此等入辛者库之人,永不叙用,永不准考试。又查得,入包衣三旗辛者库之满洲、蒙古三百余人,照例按比份分给管领当差。汉军五百五十余口,俱拨给庄屯,充额丁。臣详思,此等拨给庄屯之人,不仅庄头不能得力,白养活伊等,且伊等闲居,长此以往,渐不得培养。然此等人之父祖内,或系殷实之家,或系于大臣职任上行走,不可谓未稍加勤奋效力。今与逢恩诏宽免之人相比,罪轻、欠银两少者,亦不可谓无有……伏祈降特旨,除其中真正治罪入辛者库之人不议外,将所有因钱粮不能偿还而入辛者库之人原案缘由,伊等祖、父原系何人之处,俱缮明,送刑部,其应否宽免之处,由部分别开列,奏请谕旨可也。(39)
综上可知,入辛者库为奴之“阿哈”与被赏赐的“阿哈”并非同等身份的指称,辛者库从性质上虽是“奴”的构成部分,但他们有自己特有的名称,与直接称之为“阿哈”者不同,辛者库的领有者是那些占有包衣组织的皇帝和宗室王公,而非普通的官员或旗人。
在清初乃至清代,由于“主仆”关系中的“仆”是以阿哈为主体的,甚至包括“诸申”在内的多种身份地位的被领属者都可以笼统地称之为阿哈。所以,阿哈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奴仆”概念,既有抽象的“奴仆”属性,也有具体的身份特质。就具体指代来看,阿哈则是旗人、官员乃至包衣的奴仆;“包衣阿哈”与“阿哈”身份相同,但是有使用范围和语境的不同。入辛者库为奴则是“阿哈”中的特殊群体,他们由包衣组织管理,应该视为“包衣”群体的附属部分。
三、包衣与家人
笔者十分赞同赵阿平的观点: 特定的文化与特定的语言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联系。一个民族的语言总是体现着这个民族认识世界的方式,承载着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心理思维与历史环境。尤其是由于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而形成的词语,更体现出独特的文化涵义。(40)所以,仅仅熟悉掌握这些词汇的语言意义与语法规则是不够的,而要探寻这些“语汇”背后的政治和文化内涵。清代史料中的“家人”一词,就是具有这种政治与文化内涵的语汇。
众所周知,“家人”是清代史料中一个常用于指称奴仆的词,是满语汉译直译而来的词汇,原文为“booi”或“booi niyalma” ( 档案汉译过程中有时也译为包衣人) 。最早将包衣对译为家人的史料,应该是《满洲实录》记努尔哈赤起兵之初事时,将booi loohan 译为“家人洛汉”; 将booi yambulu uringga 译为“家人延布禄、武凌噶”等。
就语言学本义而言, “包衣”就是“家人”的说法并无不妥,但是,只要我们仔细梳理有关概念出现的语境并辨析其涵义时,仍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笔者尤其要提示的是,作为身份指称的概念,无论包衣,还是家人,其含义和用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指称的人群也在发生变化。因而,笼统的解释和运用,必然会带来问题。这里,笔者主要通过爬梳史料的方式,尝试揭示其本来的意义。
( 一) 满文汉译中的“家人”
在清初满文档案汉译过程中,汉译文中“家人”的满文原词有两种情况: 一是包衣booi; 一是包衣人booi niyalma。
“包衣”汉译为“家人”的事例,首次出现在天命三年八月十三日的记事中: “命晒打收获之谷。著纳林、殷德依二大臣为主,率诸贝勒之庄丁家人八百名至距边二十里处打谷。”(41)“家人”之主是八旗贝勒,即努尔哈赤家族成员。同年的另外一条史料中, “家人”称谓被用于明人身上: “攻克抚顺城时,俘获李参将家人一名通事一员,明帝家人十名。今将其五人释还。”(42)显然,抚顺明将和明帝的家仆与满族社会中的“包衣”身份并不能等同,但是满文书写者在记录时,只能选择含义接近的词汇。不过,有意思的是,此处“包衣”又与“明帝”连在一起,又与上文中“包衣”本义接近。
档案汉译中将“包衣人”译作“家人”的情况也比较常见。如《满文老档》汉译本记载: 天命六年十月,夸泰吉因纵容家人与汉人私行贸易,不纳税,违法行商,革其游击之职。(43)八年四月“都堂书谕: 一备御率汉人五百及千总一员,兵丁二十五人,千总携父母妻子,又十二名兵丁携妻子,驻于东京城。其家人仍居原处耕田。”(44)五月,“汗对八贝勒家人曰: 陈放于宴桌之物,计麻花饼一种,麦饼二种,高丽饼一种,茶食饼一种,馒首、细粉、果子、鹅、鸡,浓白汤各一种,并大肉汤。著将此言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45)。
从上述包衣人所涉的领属者看,既有兵丁,也有八旗旗主; 从其所承担的事务看,包括代主经商、种地和制作饭食,符合“家仆”的身份特征。由此可知,在清初满文档案中,包衣人适用于不同身份的“主人”,这一点与汉文文献中的“家人”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大体可以等同。这一现象似乎印证了郑天挺先生认为包衣人最初是对所有家仆的称谓,旗制出现后才逐渐成为特称的观点。由于八旗制度从创制到完善有一个过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包衣或包衣人之用法不明确的情况仍然存在。
不过,比较入关前满文史料中的包衣booi和包衣人booi niyalma,虽然在汉译过程中均被译为“家人”,但是在具体的历史叙述中,他们之间似仍有差异,即一般情况下,“包衣”的主人几乎都是努尔哈赤、皇太极及其家族成员,而包衣人则有指称八旗将领、官员或普通兵丁家仆的情况。这一点,也可在《清实录》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 二) 汉文本《清实录》中的“家人”
通过汉文本的《清实录》,我们可以找寻在满文表达中的包衣和包衣人,在清朝汉文官书中是如何表述的,进而分析其间的异同。通中是如何表述的,进而分析其间的异同。通过对《清实录》的爬梳,其中有关“家人”的隶属关系的记录大概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旗主家的,一类是旗主家的。
崇德元年十一月初五日纪事:
叶克舒,出边不收后队; 纵其家人一名及旗下二人乱行被杀; 擅入兄礼亲王及多罗郡王家人所得铺子,抢劫六处,其以护桥不令王之家人过桥; 殴打牵驼之人,斩杀家人所俘男童一人,逼问为何将岱松阿所获二骡送给王之家人,竟将岱松阿所获二骡以进献为名攘取之; 出边时败遁。以此四罪,罢固山额真任,革其职,罚银六百两,夺其俘获。(46)
叶克舒,满洲正红旗人。时任固山额真,此次为随武英郡王阿济格征明。叶克舒非旗主,故“纵其家人”之说,应是指其家仆,身份为八旗户下家奴。同时又提到“兄礼亲王及多罗郡王家人”,此处的“家人”未明确言其为“包衣佐领”成员,从前后行文看,应是跟役,此“家人”必定与其主关系密切。
崇德三年九月,正红旗固山额真杜雷,先是隐匿家人黑勒攻城时越旗乱走罪,又隐匿家人噶布喇盗马罪,又藏匿“知济南府德王埋藏金珠处所”证人,“俟包衣宁塔海等出城,乃乘夜令人开窖私取金银珠宝携归。”获罪革职,罢固山额真任。黑勒,鞭一百,给礼亲王为奴。(47)
结合以上两处记载可以看出,《实录》中在述及“家仆”身份的对象时,分别出现了“家人”和“包衣”两个概念,说明包衣与家人不同; “家人”的主人是固山额真杜雷(48),非旗主。“包衣”的主人文中未交待,说明这是不言自明的。根据崇德三年的档案记载,宁塔海为正黄旗包衣牛录章京,是年十二月,宁塔海牛录下苏拜,因其妻三次求神,将家产耗尽。为此奏上以闻。皇太极命包衣大伊赖核查,伊赖因袒护苏拜夫妇,以徇情罪鞭一百,贯耳鼻。(49)所以,宁塔海是皇帝的包衣。这个事例说明,此时《清实录》中,“包衣”的隶属关系已有特指了。下面一条史料更能说明这一点。
崇德八年六月己卯,皇太极谕诸王贝勒贝子公等曰: 此番出征,各旗王贝勒贝子公等家人,获财物甚多,而各旗将士所获财物甚少……归公财物,朕皆赐出征之王贝勒及各官等……内帑积储,朕躬行节俭,用之有余。时时辄行赏赉。又加以两旗及包衣人等所获,岂虑不敷所用耶。(50)
此处“家人”之主是各旗王贝勒贝子公等,皇上则用“两旗及包衣人等”予以区分,“包衣”为皇上所属的意思是明确的。康熙十八年七月,在一道上谕中,康熙帝对包衣下人及诸王贝勒大臣家人侵占小民生理、干预词讼、肆行非法等行为进行申斥。(51)二十二年九月,刑部等衙门议准对有关违法行为的处置办法:
旗下家人庄头等在外倚势害民、霸占子女、把持衙门及人到家捆缚打死者,内包衣人将该管官降级留任,王贝勒贝子公家人将该管家务官降级留任,民公侯伯大臣官员家人将伊主降级留任,系平人鞭责。著为令。(52)
这里明确了“家人”是在与“包衣”相对的情况下使用的概念,以“包衣”指代皇属包衣,而所有贵族官僚人等的私属用“家人”,说明“家人”逐渐成为一般奴仆的称谓。值得注意的是,《实录》中记载的“家人”的身份,不仅指下五旗“家仆”,而是范围更广。
顺治六年九月,刑部奏称,靖南王下旗鼓刘养正牛录章京张起凤等、兵丁马四等六人,隐匿包衣董得贵牛录下鞍匠王可义家人王三等。(53)
董得贵为正黄旗包衣第四参领第一旗鼓佐领,鞍匠王可义为旗鼓下包衣,而王三则有两种可能,或者为王可义的子侄等家人,或者为其家仆。但不会是旗鼓佐领在籍之人。所以,包衣的奴仆,也可以记为“家人”,而此“家人”则属于包衣户下家奴(54)。又如,雍正九年二月,谕八旗大臣等:
满洲、蒙古、汉军及包衣佐领下家人内,有汉仗好,行走历练,能受辛苦,且长于鸟枪弓箭者,著拣选二千名,发往西路军营备用……伊等凯旋之日,俱准为另户(55)。
显然,此处“家人”是指“户下家奴”,因为所涵盖的“家人”,不仅有满洲八旗,也有蒙古、汉军,另有包衣佐领下。并提到凯旋日可“另户”, 证明“家人”原为“户下人”,而非有包衣旗籍的“包衣”。“包衣”立功后,改变其身份的办法是“抬旗”。而此类“家人”在满文中写作“包衣阿哈”,如顺治年间满文档案有近似的记载:
董德贵牛录下鞍匠李策荣之包衣阿哈陈有功等二丁善织布,将其带来北京,使与其主人同住……雕匠高明之包衣阿哈高凤林善织布,将高凤林等二丁带来北京,使与其主人同住……高洪华牛录下张大披甲已在此处,其包衣阿哈罗古等三丁,曾捕鹞鹰,将彼等带至北京,使与其主人同住。(56)
又如“八旗佐领下男丁少者,可从开户以及包衣阿哈中弓马娴熟者选取披甲”(57)。包衣阿哈是普通旗人下家仆,是雍正帝所谓“极鄙贱之人”,被称为“开户奴才”,并禁其开户后认族为民。(58)
可以确认,在康熙朝以后, 官书中的“家人”主要是非包衣籍奴仆的专称,他们与包衣不但有旗籍与非旗籍的差别,更有在教育、考试、为官甚至法律特权等方面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待遇的巨大差异。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光绪十八年九月,步军统领衙门上报一起“王府呈送包衣家人出首谋逆人犯”事件,据称豫亲王府交出包衣闲散翟洪光、禀揭庄头李作林之胞兄李翠林及其子李春台,于上年四月在朝阳一带演习道教,纠夥谋逆。(59)这里特别表述为王府呈送的是“包衣家人”,后文具体指出具有包衣身份的是翟洪光,其他则称是庄头父子。清军入关后大量的投充庄头,没有纳入管领下管理,因而不具备独立包衣旗籍,故而此处称其为家人。
实际上,除《实录》外,其他如《清朝文献通考》、《东华录》、《八旗通志》、《起居注》等官方文书中,“家人”之谓,均指称旗人、官民等所属的户下“奴仆”。(60)
通过以上例证,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个事实,就是在清代官方汉文文献中,一般的“奴”、“奴仆”相当于满文“aha”的汉译;“家仆”、“家奴”、“家人”则相当于“booiaha”、“booi niyalam”的汉译,不存在音译的“阿哈”或“包衣阿哈”的用法。汉文中保留的“包衣”音译称谓,用以指称隶属于包衣佐领下的成员,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家奴、家人。清代汉文文献中的“家人”,主要是指在清代社会中存在的大量的买卖人口和失去自由的奴仆,他们隶属于旗人、官宦、豪绅之家,这些被称为“家人”的奴仆,他们在旗籍管理中多被称为“户下人”,其地位和身份与“阿哈”和“包衣阿哈”一样,是一般意义上的“奴仆”阶层。
四、作为身份称谓的“包衣”
《满洲实录》中最早出现的记载家仆的一个词汇是“boigon i niyalma wukame”( boigon,有家产、家业、人户之意,即指属于家产的人户,与ukambi 连用,就是逃户、逃人之意)(61)。是时,努尔哈赤的追兵,到达尼堪外兰躲避的明朝边境,以为尼堪外兰得到明守军援助,便不再靠近,而是在附近安营扎寨。当晚,随同尼堪外兰出逃的“boigon i niyalma”又逃回来,告诉努尔哈赤,明守军实际上拒绝接收其主。之前的记述曾经提到,此次尼堪外兰出逃时,放弃了军队人民( cooha irgen) ,只携带了妻、子逃离,所以可以肯定,和尼堪外兰在一起的除了亲人就是贴身伺仆,这个告密的人,一定是家仆。
与后来的“包衣”含义更为接近的记载是“帕海”的身份: “sure beilei boo i pahaigebungge niyalma”( 直译为: 淑勒贝勒家的名叫帕海的人)(62),学界多将“帕海”视为“包衣”,但是《满洲实录》汉译文译为“部落”;另外“包衣”作为身份称谓出现后,均书写作booi,即boo 与i 连写。所以,严格地说,此处帕海并没有直接贴上“包衣”的标签,但是从其身份看,具有包衣的特征。
有关记载中明确出现“包衣”指称是在万历十二年( 1584) 四月,有人欲偷袭努尔哈赤,被努尔哈赤以刀背击倒,喝令家人缚之。此处“家人”即是booi niyalma; 随后更确切地称“booi loohan” ( 包衣洛汉,《武录》记为家人老汉) ,此处“包衣”是作为“身份”名词出现的,从所述情境看,洛汉或老汉,应是家仆身份。
再次就是万历十三年( 1585) 四月,努尔哈赤征哲陈部,因族人惧战,只率弟穆尔哈齐与家人延布禄、武凌噶,冲入敌阵,遂有以4 人战胜800 人之佳话。(64)如前述,此时起可以确定,“包衣”作为指代身份的名词已经开始使用。(65)二十一年( 1593) ,海西四部纠合兵马,劫掠满洲属地,努尔哈赤出兵反击,其时,哈达贝勒蒙格布禄马扑地,危急关头,“包衣”泰穆布禄将自己的马让给主人,使其脱离危险。(66)
以上事实说明,包衣作为“家仆”或“内臣”的称谓应该是女真社会的传统,在入关前形成的满文档案文献中,虽然“包衣”一词与“家人”在语义上相同,但是,正如前辈学者所指出的,随着包衣组织制度的完善,“包衣”逐渐成为“包衣组织”下人的专称。其实,在满文档案汉译过程中,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其中的差异,故而保留了音译的“包衣”,以标识其作为汗( 皇) 家所属的身份。这一点,以下保留“包衣”音译的事例可以说明。
如天命六年闰二月,提到“汗之包衣”宁善之女配婿一事。时司膳喀萨里之子,欲聘宁善之女,嘱托雅荪、阿胡图请于汗,汗以其女已先聘于匠人浩塞之子多尔衮而拒之,并罪其请托之举,撤喀萨里司膳之职,逐入牛录( 指从内牛录到外牛录) 。四月, “汗之包衣”福汉,因窃绸衣给其外孙多铎,被守门者所执,审实后将其本人和外孙均杀之。“汗之包衣”伊拉钦,因直言举发满都赖、隋占所犯之罪,升为备御,著领五牛录。五月,“汗之包衣”德兴额往屯摘果; “汗之包衣渔户”韩楚哈、顾纳钦、络多里、阿哈岱因掠杀路旁汉人,夺其财物,审实后,杀为首者阿哈岱,其余三人鞭五十。(67)七年正月初十日,命“汗之包衣”纳彦率奉集堡所属空托模屯人88 口、44 丁,前往费阿拉。八年二月初七日,“汗之包衣”郭仲吉之妻等往汤泉水源处焚纸,被割耳鼻,划破其口,用刑三日而后杀之。(68)天命九年努尔哈赤“叙功”,述及有包衣松阿尼等在乌拉之战时受伤、包衣乌岱在扎库塔、乌拉分别受伤、包衣西拉巴死于乌拉。(69)
不仅在满文汉译中如此,即使在清历朝《实录》中,也有大量的“包衣”称谓留存,如“包衣宁塔海”(70)、“皇上包衣”(71)、“包衣董得贵”(72)、“包衣兵五百名”(73)、“八旗汉军、包衣、无品笔帖式、乌林人及闲散人等”(74)、“包衣披甲”(75)、“包衣人员”(76)、“柱儿虽系包衣”、“张永贵为包衣世仆”、“包衣陋习”、“包衣人等”、“包衣庞大庞二庞四庞五兄弟四人”、“包衣诸人”(77)、“屯居包衣人丁”、“正黄旗包衣维勤、德润”(78)、“王公所属包衣人等”、“尹同以包衣旗人”、“包衣达春瑞”、“包衣人讷海”(79)、“包衣翟洪光”(80)。等等。
以上这些出现在档案和《实录》中的“包衣”,其主人不是皇帝就是宗室王公,印证了“包衣”与努尔哈赤家族的特定关系,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家仆的涵义所能替代。值得注意的是,实际上在清代的辞书中,解释为“奴仆”的词汇有多种,除了阿哈外,尚有一辈奴、二辈奴、三辈奴、四辈奴、家生子、世仆、侍婢、老婢、散跟奴仆甚至诸申( 满洲奴仆) 等等,但这些称谓均与包衣无关; 与包衣有关的称谓则是八旗中的包衣组织及其官称,如包衣牛录、包衣大、内务府总管(与房屋有关的词汇除外) ,这或许也可以再次证明包衣的含义与汉意中的奴仆无关。
在清代,“包衣”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八旗社会中占有重要的组织资源。根据《八旗通志初集》的记载,上三旗共计有包衣佐领35 个,管领30 个。下五旗包衣共有50 个佐领,40 个管领,30 个分管,15 个管辖。综计隶属于八旗的包衣佐领85 个,管领70 个,30 个分管,15 个管辖。乾隆九年告竣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全书记载有名的上三旗包衣满洲姓氏有317 户,包衣汉姓164 户,包衣蒙古姓氏83 户,包衣高丽姓氏73 户; 总计637 户。下五旗包衣满洲姓氏346 户,包衣汉姓47 户,包衣蒙古姓氏55 户,包衣高丽姓氏55 户; 合计503 户。(81)对于这样一个满族社会中有影响而庞大的群体,对其身份和地位进行翔实的研究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笔者愿再次强调以下两点认识:
其一,无论包衣、阿哈还是家人,这些词语并不是普通的语汇,它内涵着时人对所描述的“群体”的一般性特征的认识、判断。以往研究者对于“奴仆”的各种称谓之间的差异关注不够,导致其背后的身份涵义和群体特征被忽略了。致使学界笼统地使用或解释这些概念,影响了我们对清代主仆关系和八旗社会的认识。
其二,准确地说,“包衣”是努尔哈赤家族的旗籍“世仆”,或曰“家臣”、“内臣”(82)。包衣之谓“仆”,与诸申之谓“仆”的性质相同,是清代旗人社会主属性关系下对被领属者的一般性描述。所以,将有清一代具有特殊身份的“包衣组织”成员,定性于一般意义上的“家仆”、“家奴”,甚至与“阿哈”、“包衣阿哈”等同,客观上造成了偷换概念的结果。学界的这种混淆,不仅影响到我们对清代奴仆群体的准确把握,也会影响到对清初社会和八旗组织结构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