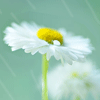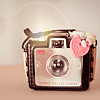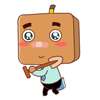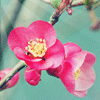罗之恋(暹罗之恋)我和依依走在笔直的滨河路上,河岸边的柳树垂下绿绦,迎着风向我们打招呼;挺拔的白杨在风中沙沙作响,似乎在为隔岸如繁星点缀的丁香树演奏爱的序曲。天空中,风筝静默地享受着风的爱抚。
望着风筝,我轻叹道:“好想去放风筝。”刚说完,依依就拉起我的手朝广场跑去。依依为我挑选了一只大号的画着笑脸的风筝。整个下午,我们都在广场放风筝。当我把线轴转到尽头,她脸上的喜悦远远超过了飞到最高处的那张笑脸。她欢喜地接过风筝,学着我的样子,时而拽拽线,时而转动把手收收线。风,忽然小了,风筝开始朝下栽。她慌张地不知所措,握着线轴的手拉扯着。我握住她的手,将把手拼命回转,终于赶在风筝坠入河里之前将它收了回来。我长舒一口气,松开依依的手,朝她笑着,用弯曲的食指在她白皙的布满细密汗珠的鼻尖上刮了一下,亲昵地说:“小笨蛋。”她的眼眶竟然湿了,扑到我怀里哭了起来。我搂着她,笑着说:“我是大傻瓜,总行了吧?”她笑了一声,可还是依偎在我的怀里,我的胳膊轻轻搭在她的腰间,她轻微而又温热的气息打在我的脖颈上,泛开一片红晕。我低下头,在她耳边轻轻说:“起来吧,你看,别人都在看我们呢,肯定都以为我们是同性恋。”她终于从我怀里出来,可她的体温却留在我的半个身体里,灼烧着我。她像小猫一样怯生生地瞄了瞄周围的人,说:“谁在看我们?”

我一边将风筝拆开装进袋子,一边说:“好了,我饿了,走吧。”
她一把夺过袋子,打在我身上,呵斥道:“好啊,你骗我!”
我皱起眉头,问:“你个妖怪,我有几个胆啊?敢骗你?”
她打量了我一下,仰起头,嘟起嘴,说:“谅你也不敢。”一把将袋子塞进我怀里,挽着我的胳膊,要我陪她去吃火锅。
外公去世后的七天里,我都在老家。每天和兄弟姐妹们穿着孝衣,跪在灵堂里的外公棺木前焚香烧纸,看着熟识的,或不认识的人们前来吊唁。在灵位前,人们说些节哀顺变之类的话,踏出门槛,又开始寒暄,说说笑笑。或许,生与死的界限,就像灵堂与屋外之间的门槛一样,只是不能如此随意地跨来跨去。可当我走出灵堂去吃饭时,才发现自己无法融入到大人们的玩笑里去,我也终于明白:即便我走出灵堂,我也走不出哀伤,即便人们跨入灵堂,也跨不进这死亡的阴影。从老家回来后的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都未与外界联系,整日沉浸在关于死亡的冥想里。生怕父母、自己也会死去。黑的夜晚,总感觉有一股势力在向自己逼近,吓得打开台灯,在光亮中张望了半天。平静之后,再关掉灯。不一会儿,便感觉那股力量又朝自己袭来,惶恐不安。又打开灯,张望,平静,关灯……每个夜晚都是如此,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何时入睡的。

依依到我家来看我。看到依依,我才发现,自己差点都忘记了还有这个朋友。
依依说:“难受,就哭出来吧。”
我的眼泪不听使唤,没节制地流了出来,我看不清她的样子。她走过来站在我面前,一只手轻轻拭去我面颊上的泪水,一只手搂着我。我哭得越发厉害了,紧紧抱住她,靠在她的肩头拼命地哭,把积攒了二十天的眼泪统统哭了出来。
我在图书馆的文学书库里找书,收到了依依的短信:“下雨了,我没带伞。我在广场,国芳百盛。”我回复:“一会就到。”
找到了余华的《活着》和高行健的《寒夜的星辰》,拿着书朝门口走,听到了两个管理员在聊天。男的说:“周末也没个休息。”女的说:“现在来图书馆的人,脑子里都缺根弦。”我刚好闯入他们的视线里,男人朝女人使了个眼色,女人瞟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我也没作声,把书和借书证递给她。

我赶到广场,进入商场,看到依依在一家柜台前徘徊。我把拿着伞的手背到身后,走到她面前。她欣喜不已,我失落地说:“我也没带伞。”她更失落了,可又马上打量起我来,猛地转到我身后抢伞,我也一转身,说:“咦?什么时候变聪明了?”她不屑地看了我一眼,仰起头说:“切,小儿科,你身上一点儿都没湿。”我打趣道:“哟,智商见长。”她猛地打了我一下,嗔怒道:“讨厌!”我笑了笑,说:“傻瓜,走吧!”她走过来挽着我的胳膊,说:“那你是笨蛋。”
我打着伞,她依偎着我,清冷的雨中,她的体温温暖了我。一边走,我一边给她讲图书馆管理员的对话。我刚讲完,她就义愤填膺起来:“他们算什么东西!他们也天天都去图书馆,那他们是什么?”我笑了笑。她继续说:“你别理他们,我支持你,以后我陪你去。”我笑着问:“你是去睡觉,还是去让我看你睡觉?”她一把推开我,被雨淋着了,又过来靠着我,没好气地说:“都怪你,害我被雨浇!”我问:“也不知道是哪个傻瓜把我推开的?”她理直气壮地说:“要是你不气我,我能推你吗?都怪你!”我说:“那你是承认自己是傻瓜喽?”她气得说不出话来,看着我,突然抓住我打伞的手,咬了一口。她自豪地仰起头。我看看手上的牙印,恼怒地说:“你属狗的啊!”她不假思索地反问:“谁叫你属羊?”我一时语塞。她哈哈大笑着说:“笨蛋,你应该说:“狗是保护羊的,哪有这么不称职的狗?”我笑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她揉揉留有她牙印的地方说:“不疼吧?我来打伞吧。”我说:“你还是只牙没长全的小哈巴狗。”她仰起头,嘟着嘴说:“哈巴狗就哈巴狗,天天粘着你。”
我漫不经心地说:“你也就下雨天没带伞粘着我。”

她瞪了我一眼:“才不是!”
依依的男朋友冷于冰也从老家回来了。在冷于冰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的十天里,依依一直在给我打电话,多是抱怨冷于冰不给她打电话。
第一天,我说:“才走一天,你就想得不行啦?”依依说:“没有。”
第二天,我说:“冷于冰,一个大小伙子,还是长孙,回到老家自然要拜访亲戚邻居,干些活什么的,很忙的,又不像你在家闲得只能上网看电视。”依依说:“也对。”
第三天,我说:“想,就打电话呗,你有给我打电话的工夫,不会给他打啊?”依依说:“那多没面子,不要。”
第四天,我说:“可能是漫游费太贵,给你一打电话就会刹不住,所以就干脆不打,等回来再给你说个三天三夜的。”依依说:“好吧,他确实很节省。”
第五天,依依哭着说:“他心里根本没有我。”我说:“火车站小偷很猖獗,可能他的手机被偷了,又不记得你的号码。你想,号码丢了,要怎么给你打电话?他现在一定也很着急上火。”依依继续哭,我没再说话。她对着话筒哭,我静静听着,她的泪水像瀑布一样穿过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击落在我心上。她的泪水在我心上激荡了许久之后,哭泣停止了。我的呼吸像被放置在海底,深深地压抑着。她说:“我想见你,明天,广场老地方见。”我努力用轻快的语调说:“好,明天见。”嘟——嘟——她挂断了电话,她从来不对我说再见。

第六天,我到地方的时候,依依已经坐在那里了。她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们什么也没说,静静享受春日的暖阳。她以前说过,特别喜欢和我在一起,因为想说话的时候,我是个认真宽容的听众,不想说话的时候,只要和我安静地在一起,不仅不会觉得尴尬,反而会有一种安全感。现在,她靠在我肩头,我不知道能不能让她暂时忘记冷于冰,可这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
她突然说:“你要是男的多好,我就可以追你做我的男朋友。”
话到嘴边,我又改了口:“你那么麻烦,我要是男的,才不找你。”
她又沉默了,我感觉自己伤害了她。
我说:“突然想起了一句很不恰当但又十分确切的台词。”
她笑了,说:“你又犯什么糊涂?”
我问:“你要听吗?”
“你说。”
我犹豫了一下,缓缓地说:“我不能做你的爱人,但不代表我不爱你。”
她笑着说:“说得真好。”
第七天,依依又打来电话,但没再提及冷于冰。她问:“昨天你说的那句台词是出自哪里的?”我沉默了。她又问:“你在听吗?”我回过神说:“忘记了。”有些感情在某些时候是很模糊的,就像镜中花水中月一样美好,可若怀着勇气捅破那层窗户纸,剩下的,怕唯有那穿梭着冷风的破洞。

第八天,我拨通了冷于冰的电话。我问他:“你为什么不给依依打电话?”他说:“你说什么?”我说:“依依因为你不给她打电话,哭得很难受。”冷于冰说:“原来是这样。我走之前,我们吵了一架,我以为她不会原谅我了。我也在等她的电话。”我哑然失笑:“我跟她说你的手机丢了,你自己想办法跟她解释吧。”
第九天,依依打电话来要约我明天出去玩,我想了想:“不行,明天我姐姐过生日,已经约好了的。”
第十天,依依打来电话,语调很轻快:“你知道吗?你说的没错,他是没办法和我联系。冷于冰,这个糊涂鬼,出门的时候忘记带手机了。坐到火车上才发现。他又从来不记电话号码。他老家也没电脑。总之,他也很想我。今天早上,我接到他的电话,让我下楼,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他拿着一束玫瑰花在……”我不耐烦地打断她:“好了,好了,你个神经病,成天瞎想,啥事没有,都能让你想出麻烦来。好了,我还有事,先挂了。”我想,以她此刻的心情,应该不会介意听一听“嘟——嘟——”的声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