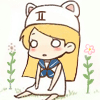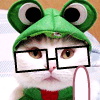天边的一朵云(天边的那朵云)

几十年了,西天边总好像有一朵白云悠悠飘动,不散去。
是几十年了啊。记得是那年春夜,天气还冷着呢,我和一位女同学在那个小站候车。我俩是省农校学生,是从省城下来实习的。
下夜3点她乘火车、天明我乘汽车分赴两个年县去防治小麦吸浆虫。
那时候的人还不会破费公家的钱,拿着公款也舍不得花。且不说豪华旅社,连一般旅社也不住,咋省钱就咋对付。候车室外茶摊备有竹躺椅,躺椅上有薄褥,我俩各租一个,联床露宿。
我俩说着话儿,也跟卖茶大娘说着话儿。
我俩是少男少女。当时学校领导不知为什么忽略了这个就让我俩结伴下乡,就像是把两只家养的鸽子放飞了。
那时农校光有寝室没有教室,坐小板凳露天学习。下雪了,回到寝室,寝室也窄狭,只好登床学习。男生一头,女生一头,拥衾抵足,写字垫板放在被子上,低头写字,半天不说一句话。
也曾在豫东沙区里艰难同行,一只水壶转口吮吸,狂风里也有谁扯过谁一把。晚上住进一个大宅第,石阶苍苔,幽深空荡,跟《聊斋志异》中描写的那样。
夜间我们几个男生把没有罩子的煤油灯烧得通亮给女生壮胆,颇像关云长“秉烛窗下”,至今自豪。
卖茶大娘精神好,不倦地陪我们说话,破扇子忽啦忽啦,炉火一亮一亮。
竹椅扶手上潮湿了,知夜露已降。我们在各自的躺椅上轻轻滚动,薄褥越裹越紧,再滚动,竹椅喀喀地响,我俩格格地笑,笑露宿之惬意。
一枚大柑橘没吃完,伸手递给对方,对方仍吃不完,又返回。
火车长鸣一声,弯月向西方坠落。我们没有睡意,有点冷。于是就起劲地讨论到农村如何教会农民使用工具杀灭害虫,争取小麦好收成。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睡梦中知道自己睡得很甜,等我醒来时,我同学的躺椅空了,人和薄褥都已不见。
卖茶大娘告诉我说:“你的同学进站了。”
我摸摸身上发觉我盖的是两条褥子。大娘说:“她看你睡着了,慢悠悠把她的褥子盖在你身上。你也不知道,你也真是。”火蓦地闪亮,大娘喜眯眯的。
大娘从炉膛里掏出一块烤红薯,说:“给,她给你留的。”
烤红薯很暖和,我双手握住,不想马上往嘴里送,看着西天弯月发呆。
弯月旁边有一朵白云,梦幻般地让人心颤,那朵白云就算是贴在我心上了。
天亮,我乘汽车去另一个县了。
谁会料到打那以后风云变幻,人事沧桑,至今也没有再见过她:几十年里,只有关于她似有似无的传闻。她的面影已模糊如一团云,在我脑海中没有一个定位。
人生一个小别离竟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前不久,我见到另一位也是几十年没有见过面的女同学,领着她的儿子和女儿,都已老大老高了。
我们恍若转世再见,她一握住我手就满眼泪花。她儿子女儿齐声向我叫叔叔,她哽咽纠正:“叫舅舅的!”这称谓先使我 一愕, 再后便泪水涌流。
少年时代的同学感情是个独特的结构,多半还具有兄弟姐妹的同胞情分。彼此无意识将此情分固守住,埋在心底无由言说,今日在这儿女同在的场合,如同一个真实的消息或重大结论,真真切切地表白出来了,使彼此感情上意外地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
然而,我的那位同学呢?西望天边白云还在,成为我对那位也许是远嫁了或下嫁了且不知命运如何的姐妹的无涯之凄。
推荐您阅读更多有关于“”的文章